關於大悲咒,
8/11/2021
大悲咒
佛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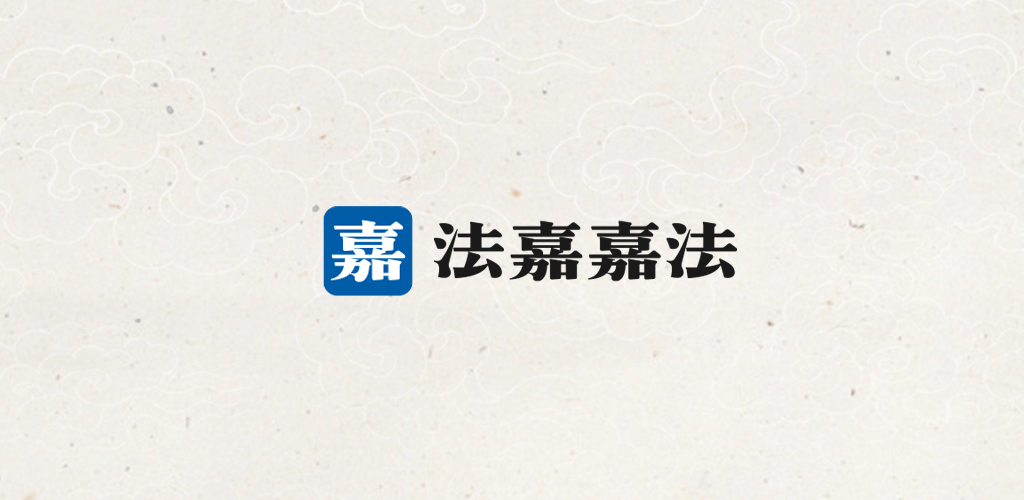
藏經閣裏大悲咒第16是否不全,有漏?
 法嘉宗智 回答
法嘉宗智 回答
種類分析
《大悲咒》按照內容文字的多少,有廣、中、略三種版本的分類。
【伽梵達摩略本】
略本系多是圍繞“伽梵達摩”譯本來抄寫,另外也有單獨類的簡化抄本和註釋本。
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》伽梵達摩譯[1]
這一最早也最流行的大悲咒版本,雖流行度最高,但也最為凌亂,甚至譯者翻譯原貌都不很清楚,且咒文並不連貫。
真實性的確定:該譯本《大悲心陀羅尼經》最早於《開元釋教錄》有載:“智升”在詢問其他梵僧後,得知該經是有梵本依據的,所以確認為真經。[2]但本經梵文本已無從查找。[3]雖然至今各版漢文大藏經中,《大悲心陀羅尼經》獨有“伽梵達摩”譯本;但在經藏以外,學者發現了本經同源梵本的異譯本,[4]因此可以肯定伽梵達摩譯本的真實性以及《大悲咒》的真實性。
流行本的形成:現今流行的“伽梵達摩”經本,是“伽梵達摩”在“于闐”所翻譯,之後即回國。本經是從于闐通過抄寫而不斷傳到內地,其翻譯並非官方組織的譯經,而是民間的抄寫流傳。本經原梵本已不存在,現今的流行本多以《大正藏》為底本,而《大正藏》此伽梵達摩經本是以《明藏》為底本,但此版本已是極晚期的版本。[5]本經因傳抄廣泛,導致在抄寫過程形成越來越多的錯誤並不斷演變擴大。在這個變化過程中,有些地方的改變已完全影響了原來的梵文音貌。這些變化並非某梵本的出現被修改,而是原譯本不斷傳抄而形成。所以不存在早期本的缺失或遺漏,而早期的版本才是真實狀況。[6]
變化的形式:從伽梵達摩各抄本的差異變化發現,人為抄寫,即使是短時期的同類抄本也有很大變化,何況一篇經咒長期不斷傳抄,並且是廣泛的繁衍傳承,故其變化極其錯綜複雜。而事實上,《大悲咒》的錯誤不僅是傳抄的問題,有很大一部分是聽聞上的錯誤所致;[7]除了文字的不斷變化,《大悲咒》也發生了一些形態上的變化:在傳抄時出現了各種圍繞咒文的簡化抄注本,[8]由於此類抄本的方便實用,故比經本傳抄量更大,而《大悲咒》本身也不排除受到這種變化的影響。
衍生的疑點:後期出現的各種簡化單行本,《大正藏》有兩個本子(No.1064、[9]No.1113B[10])署名“不空”譯,[11]但卻存在一些疑點。[12]經考據為傳抄時錯誤託名;[13]或為“不空”註釋;[14]或是對“不空”中本《大悲咒》的錯誤領會所致。[15]這類單行本實際都是“伽梵達摩”經本在民間抄寫的簡化,皆為後期衍生品,“伽梵達摩”是最初的唯一譯者。“不空”與《大悲咒》的確切關係是:“不空”翻譯了中本《大悲咒》;且只對“伽梵達摩”譯本進行註釋;“不空”並沒有重新翻譯過這部經。[16]
【中本與廣本】
中本系只有幾個版本且差異不大,皆是沒有經文聯繫的咒文本。內容多於“伽梵達摩”本,此處列舉三本:
①不空譯本《聖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》[15][17]此一譯本較“金剛智”的“新譯”本,其內容略有減少,但較“伽梵達摩”的譯本仍多出很多內容。
②慈賢譯本《大悲心陀羅尼》[18]與上述的“不空”本基本相同而有若干增補,不知是“慈賢”所增、梵本即有,還是“不空”遺漏。但二者為同本。
③行琳集本《聖觀自在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大陀羅尼》[19]是依據上述“不空”本又作了修訂,其中大的差異處似為依據“金剛智”的儀軌本。[16]
廣本漢文本系與其經文內容無關聯,只有“金剛智”的“新譯”名稱能對應上,其餘版本只是內容與“金剛智”本有關聯:
①金剛智新譯本《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咒》[20]為單譯的咒本,名稱與“伽梵達摩”所譯的《大悲咒》完全一致,但內容卻多出不少。經考據,該咒本是“金剛智”針對“伽梵達摩”譯本所作的“新譯”。[21]可見“金剛智”對“伽梵達摩”的咒文翻譯部分不完全認同,其所依據應另有梵本。同時該異譯本與藏文本系的《大悲咒》有很多共同點,可見“伽梵達摩”所譯《大悲咒》的完整性值得懷疑。
②金剛智儀軌本《金剛頂瑜伽青頸大悲王觀自在唸誦儀軌》[22]其中所載的《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你攞建他陀羅尼》與上述咒本有些不同,但該譯本卻與其他本較為一致,此中誰是誰非暫無法確認。
③不空註釋本《青頸觀自在菩薩心陀羅尼經》[23]此註釋本與“金剛智”的新譯本相似,咒文稱《青頸觀自在菩薩心陀羅尼》,而不是《大悲心陀羅尼》。
④行琳集本《青頸大悲觀自在菩薩陀羅尼》[19]該咒本內容是依據上述不空本為底本,由此也可證明上述經本的真實性。[24]
廣本藏文本系有很多與漢譯本相一致的經文,而且從不同角度傳播。其中有藏文本亦有漢譯本,有對應經文相聯繫也有單獨咒本,內容都很一致。
①《聖青頸陀羅尼》[25]與漢文本更接近些,或可説該本更早/地域更接近些。
②《千手千眼聖觀自在菩薩儀軌細釋》[26]
③《聖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無礙大悲心廣大正圓滿陀羅尼》[27]是唐代“法成”由漢文轉譯成藏文,但其咒文部分並沒有按照漢文本轉譯,而明顯依據了上述兩種藏文本。
④“釋迦智”譯《攝聖觀自在大悲尊陀羅尼利益經》[28]與早期藏文本差異較大,與最晚的梵文本較接近。 本經所對應的《大悲咒》比“伽梵達摩”所譯《大悲咒》,內容多出很多。[16]
廣本敦煌抄本中多有一類“伽梵達摩”經本,抄寫時將原譯的咒文部分替換為具有敦煌音譯特色的譯文,這類譯文的發音及用字都與內地的其他常見譯文不同,且多見於敦煌抄本中,也有一些藏文音譯特色。這一本系的《大悲咒》,其內容上有與藏文本系和漢文本系相同之處,還有些更似漢藏差異的折中或過渡,以及具有一些獨自的特點,這些不共特點又恰好與中本和略本有一定共性。所以類似一個大網絡,將各個不同版本間的差異與共性交織在了一起。[16]
時地分析
流傳時間:
①“伽梵達摩”譯本最早載於《開元釋教錄》(730年),且此時流行已久,故譯經必早於公元730年。“金剛智”(670-741)新譯晚於“伽梵達摩”。“不空”(705-774)譯本則再晚些。以上三種唐譯本,時間稍有先後,但屬同時代。
②“法成”(-848-)由漢譯藏本No.691,其咒文直接參考更早的藏文No.697、690兩本,其中No.697與漢文本更接近。“釋迦智”(993-1075)譯藏文No.723再晚些,該本與上述兩藏文本差異較大,而更接近最晚的梵文本,故時間在這二者間。
③敦煌抄本多基於“伽梵達摩”經本而修改,一般為唐代抄本;其內容多處於漢譯/藏文No.697、690與藏文No.723間的過渡狀態,故時間即在此中間階段。
④其餘多是以上諸本的重譯或整理。至於梵文各抄本則晚於宋代。
⑤故大體時間順序為:
1.唐譯本/藏文No.697本;
2.藏文No.690本;
3.敦煌本;
4.藏文No.723本/西夏譯本/明清譯本;
5.梵文本。
流傳地域:
①“伽梵達摩”為“西印度”人,而其譯經地“于闐”的文化交融與“北印度”關聯較大,其所依經本應反映“西/北印度”的特徵;而“不空”、“慈賢”中本與該本有很大關聯。故中略本即是“西/北印度”抄本的反映。
②“金剛智”譯本隨其攜帶而來自“南印度”。“不空”從“獅子國”帶來大量經本,又在國內收集大量遺留梵本,其譯本有中廣兩種:中本與“伽梵達摩”譯本相關,應來自國內收集,可溯源於“西/北印度”;其廣本與“金剛智”本相近,即來自“獅子國”等“南印度”一帶。因此“金剛智”、“不空”(廣)本特徵應為“南印度”的反映。
③西藏經本多是尼泊爾一側傳入:藏文No.723與後期尼泊爾梵本很相近,其地域接近“中/東印度”一帶。藏文No.697、690則與此稍異,故而時間更早或是別地傳入。
④敦煌抄本則有些獨特性,其中有與藏文本漢文本一致的,還有處於差異點過渡狀態,乃是時間、地域過渡上的真實寫照。
結論:古印度的經典多通過口誦相傳,而不注重書寫,流傳到後來即發生變化。故時間越早且越接近發源地的版本,才可能是錯誤最少的。佛教中密教部分即率先流行於“南印度”;而於佛典中,該經的宣講地“補陀落迦”也位於“南印度”的一側。因此“南印度”即為該《大悲咒》發源地,“南印度”的版本也應是相對錯誤較少的版本。而結合時間的分析,“金剛智”和“不空”的(廣本)譯本則相對較符合這一特徵。而縱使“金剛智”本來源於南印度,但也流傳了幾百年,其中局部也已發生變化;而傳至別處的版本也不一定都會錯,其中也可能還保留了部分原始信息。所以對於一些無法推敲的地方,誰是誰非並無定論。[24]
版本選擇
《大悲咒》有其發展的特殊性,而通過其內在關聯性的呈現,雖然可以解決其中多種疑問和不確定性的問題,但由於歷史發展原因,而無法確認統一成唯一的版本。佛教學者認為,對修行和持誦者而言,尚由自己來決定選擇廣、中、略的哪一版本;但對於已知的、明顯變化後的錯誤字句,如果依舊盲目依從,則並不明智。在相關研究者看來,歷史上不乏有些唸誦者依照錯誤的經咒唸誦,並不妨礙其得到效驗,但亦應大打折扣。否則只需念“笤帚”亦可成就,而不必去學習此類殊勝而方便的法門。
共3張
房山石經 不空、慈賢《大悲咒》
有佛教相關研究者的建議是:由於該咒本流傳很廣,變化很多,又咒文之密意實非表面字句可以獲得。故而縱有差異,於真正修行者而言,其影響應也不大。所以行持者可於諸本中自行抉擇,但無論採用哪一結論,都應謹記經中所言:
“唯除不善,除不至誠”;
“生少疑心者,必不果遂也”;
“唯除一事,於咒生疑者,乃至小罪輕業,亦不得滅,何況重罪”……
《大悲咒》按照內容文字的多少,有廣、中、略三種版本的分類。
【伽梵達摩略本】
略本系多是圍繞“伽梵達摩”譯本來抄寫,另外也有單獨類的簡化抄本和註釋本。
《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》伽梵達摩譯[1]
這一最早也最流行的大悲咒版本,雖流行度最高,但也最為凌亂,甚至譯者翻譯原貌都不很清楚,且咒文並不連貫。
真實性的確定:該譯本《大悲心陀羅尼經》最早於《開元釋教錄》有載:“智升”在詢問其他梵僧後,得知該經是有梵本依據的,所以確認為真經。[2]但本經梵文本已無從查找。[3]雖然至今各版漢文大藏經中,《大悲心陀羅尼經》獨有“伽梵達摩”譯本;但在經藏以外,學者發現了本經同源梵本的異譯本,[4]因此可以肯定伽梵達摩譯本的真實性以及《大悲咒》的真實性。
流行本的形成:現今流行的“伽梵達摩”經本,是“伽梵達摩”在“于闐”所翻譯,之後即回國。本經是從于闐通過抄寫而不斷傳到內地,其翻譯並非官方組織的譯經,而是民間的抄寫流傳。本經原梵本已不存在,現今的流行本多以《大正藏》為底本,而《大正藏》此伽梵達摩經本是以《明藏》為底本,但此版本已是極晚期的版本。[5]本經因傳抄廣泛,導致在抄寫過程形成越來越多的錯誤並不斷演變擴大。在這個變化過程中,有些地方的改變已完全影響了原來的梵文音貌。這些變化並非某梵本的出現被修改,而是原譯本不斷傳抄而形成。所以不存在早期本的缺失或遺漏,而早期的版本才是真實狀況。[6]
變化的形式:從伽梵達摩各抄本的差異變化發現,人為抄寫,即使是短時期的同類抄本也有很大變化,何況一篇經咒長期不斷傳抄,並且是廣泛的繁衍傳承,故其變化極其錯綜複雜。而事實上,《大悲咒》的錯誤不僅是傳抄的問題,有很大一部分是聽聞上的錯誤所致;[7]除了文字的不斷變化,《大悲咒》也發生了一些形態上的變化:在傳抄時出現了各種圍繞咒文的簡化抄注本,[8]由於此類抄本的方便實用,故比經本傳抄量更大,而《大悲咒》本身也不排除受到這種變化的影響。
衍生的疑點:後期出現的各種簡化單行本,《大正藏》有兩個本子(No.1064、[9]No.1113B[10])署名“不空”譯,[11]但卻存在一些疑點。[12]經考據為傳抄時錯誤託名;[13]或為“不空”註釋;[14]或是對“不空”中本《大悲咒》的錯誤領會所致。[15]這類單行本實際都是“伽梵達摩”經本在民間抄寫的簡化,皆為後期衍生品,“伽梵達摩”是最初的唯一譯者。“不空”與《大悲咒》的確切關係是:“不空”翻譯了中本《大悲咒》;且只對“伽梵達摩”譯本進行註釋;“不空”並沒有重新翻譯過這部經。[16]
【中本與廣本】
中本系只有幾個版本且差異不大,皆是沒有經文聯繫的咒文本。內容多於“伽梵達摩”本,此處列舉三本:
①不空譯本《聖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》[15][17]此一譯本較“金剛智”的“新譯”本,其內容略有減少,但較“伽梵達摩”的譯本仍多出很多內容。
②慈賢譯本《大悲心陀羅尼》[18]與上述的“不空”本基本相同而有若干增補,不知是“慈賢”所增、梵本即有,還是“不空”遺漏。但二者為同本。
③行琳集本《聖觀自在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大陀羅尼》[19]是依據上述“不空”本又作了修訂,其中大的差異處似為依據“金剛智”的儀軌本。[16]
廣本漢文本系與其經文內容無關聯,只有“金剛智”的“新譯”名稱能對應上,其餘版本只是內容與“金剛智”本有關聯:
①金剛智新譯本《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咒》[20]為單譯的咒本,名稱與“伽梵達摩”所譯的《大悲咒》完全一致,但內容卻多出不少。經考據,該咒本是“金剛智”針對“伽梵達摩”譯本所作的“新譯”。[21]可見“金剛智”對“伽梵達摩”的咒文翻譯部分不完全認同,其所依據應另有梵本。同時該異譯本與藏文本系的《大悲咒》有很多共同點,可見“伽梵達摩”所譯《大悲咒》的完整性值得懷疑。
②金剛智儀軌本《金剛頂瑜伽青頸大悲王觀自在唸誦儀軌》[22]其中所載的《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你攞建他陀羅尼》與上述咒本有些不同,但該譯本卻與其他本較為一致,此中誰是誰非暫無法確認。
③不空註釋本《青頸觀自在菩薩心陀羅尼經》[23]此註釋本與“金剛智”的新譯本相似,咒文稱《青頸觀自在菩薩心陀羅尼》,而不是《大悲心陀羅尼》。
④行琳集本《青頸大悲觀自在菩薩陀羅尼》[19]該咒本內容是依據上述不空本為底本,由此也可證明上述經本的真實性。[24]
廣本藏文本系有很多與漢譯本相一致的經文,而且從不同角度傳播。其中有藏文本亦有漢譯本,有對應經文相聯繫也有單獨咒本,內容都很一致。
①《聖青頸陀羅尼》[25]與漢文本更接近些,或可説該本更早/地域更接近些。
②《千手千眼聖觀自在菩薩儀軌細釋》[26]
③《聖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無礙大悲心廣大正圓滿陀羅尼》[27]是唐代“法成”由漢文轉譯成藏文,但其咒文部分並沒有按照漢文本轉譯,而明顯依據了上述兩種藏文本。
④“釋迦智”譯《攝聖觀自在大悲尊陀羅尼利益經》[28]與早期藏文本差異較大,與最晚的梵文本較接近。 本經所對應的《大悲咒》比“伽梵達摩”所譯《大悲咒》,內容多出很多。[16]
廣本敦煌抄本中多有一類“伽梵達摩”經本,抄寫時將原譯的咒文部分替換為具有敦煌音譯特色的譯文,這類譯文的發音及用字都與內地的其他常見譯文不同,且多見於敦煌抄本中,也有一些藏文音譯特色。這一本系的《大悲咒》,其內容上有與藏文本系和漢文本系相同之處,還有些更似漢藏差異的折中或過渡,以及具有一些獨自的特點,這些不共特點又恰好與中本和略本有一定共性。所以類似一個大網絡,將各個不同版本間的差異與共性交織在了一起。[16]
時地分析
流傳時間:
①“伽梵達摩”譯本最早載於《開元釋教錄》(730年),且此時流行已久,故譯經必早於公元730年。“金剛智”(670-741)新譯晚於“伽梵達摩”。“不空”(705-774)譯本則再晚些。以上三種唐譯本,時間稍有先後,但屬同時代。
②“法成”(-848-)由漢譯藏本No.691,其咒文直接參考更早的藏文No.697、690兩本,其中No.697與漢文本更接近。“釋迦智”(993-1075)譯藏文No.723再晚些,該本與上述兩藏文本差異較大,而更接近最晚的梵文本,故時間在這二者間。
③敦煌抄本多基於“伽梵達摩”經本而修改,一般為唐代抄本;其內容多處於漢譯/藏文No.697、690與藏文No.723間的過渡狀態,故時間即在此中間階段。
④其餘多是以上諸本的重譯或整理。至於梵文各抄本則晚於宋代。
⑤故大體時間順序為:
1.唐譯本/藏文No.697本;
2.藏文No.690本;
3.敦煌本;
4.藏文No.723本/西夏譯本/明清譯本;
5.梵文本。
流傳地域:
①“伽梵達摩”為“西印度”人,而其譯經地“于闐”的文化交融與“北印度”關聯較大,其所依經本應反映“西/北印度”的特徵;而“不空”、“慈賢”中本與該本有很大關聯。故中略本即是“西/北印度”抄本的反映。
②“金剛智”譯本隨其攜帶而來自“南印度”。“不空”從“獅子國”帶來大量經本,又在國內收集大量遺留梵本,其譯本有中廣兩種:中本與“伽梵達摩”譯本相關,應來自國內收集,可溯源於“西/北印度”;其廣本與“金剛智”本相近,即來自“獅子國”等“南印度”一帶。因此“金剛智”、“不空”(廣)本特徵應為“南印度”的反映。
③西藏經本多是尼泊爾一側傳入:藏文No.723與後期尼泊爾梵本很相近,其地域接近“中/東印度”一帶。藏文No.697、690則與此稍異,故而時間更早或是別地傳入。
④敦煌抄本則有些獨特性,其中有與藏文本漢文本一致的,還有處於差異點過渡狀態,乃是時間、地域過渡上的真實寫照。
結論:古印度的經典多通過口誦相傳,而不注重書寫,流傳到後來即發生變化。故時間越早且越接近發源地的版本,才可能是錯誤最少的。佛教中密教部分即率先流行於“南印度”;而於佛典中,該經的宣講地“補陀落迦”也位於“南印度”的一側。因此“南印度”即為該《大悲咒》發源地,“南印度”的版本也應是相對錯誤較少的版本。而結合時間的分析,“金剛智”和“不空”的(廣本)譯本則相對較符合這一特徵。而縱使“金剛智”本來源於南印度,但也流傳了幾百年,其中局部也已發生變化;而傳至別處的版本也不一定都會錯,其中也可能還保留了部分原始信息。所以對於一些無法推敲的地方,誰是誰非並無定論。[24]
版本選擇
《大悲咒》有其發展的特殊性,而通過其內在關聯性的呈現,雖然可以解決其中多種疑問和不確定性的問題,但由於歷史發展原因,而無法確認統一成唯一的版本。佛教學者認為,對修行和持誦者而言,尚由自己來決定選擇廣、中、略的哪一版本;但對於已知的、明顯變化後的錯誤字句,如果依舊盲目依從,則並不明智。在相關研究者看來,歷史上不乏有些唸誦者依照錯誤的經咒唸誦,並不妨礙其得到效驗,但亦應大打折扣。否則只需念“笤帚”亦可成就,而不必去學習此類殊勝而方便的法門。
共3張
房山石經 不空、慈賢《大悲咒》
有佛教相關研究者的建議是:由於該咒本流傳很廣,變化很多,又咒文之密意實非表面字句可以獲得。故而縱有差異,於真正修行者而言,其影響應也不大。所以行持者可於諸本中自行抉擇,但無論採用哪一結論,都應謹記經中所言:
“唯除不善,除不至誠”;
“生少疑心者,必不果遂也”;
“唯除一事,於咒生疑者,乃至小罪輕業,亦不得滅,何況重罪”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