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陀對於誹謗唾棄自己的人會如何做?
6/3/2018
达摩四行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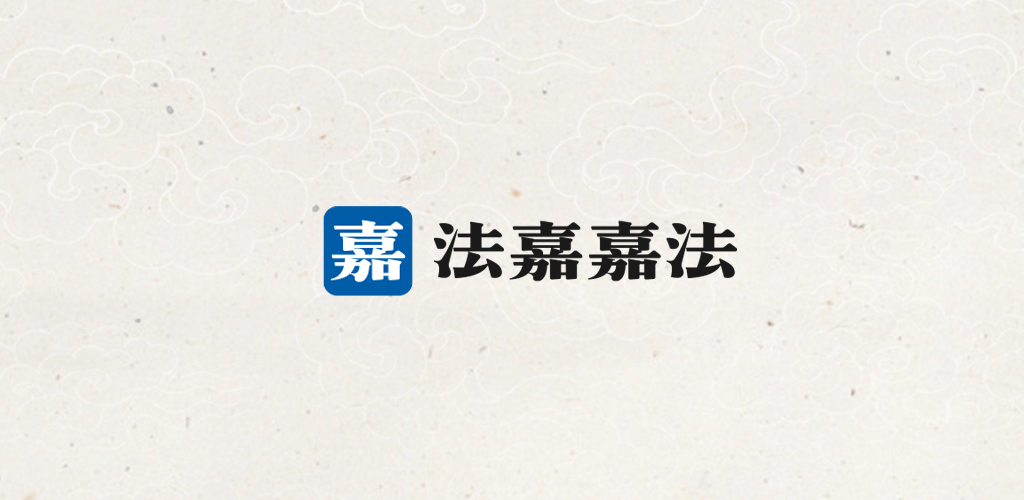
 法嘉宗智 回答
,獲得 1 贊
法嘉宗智 回答
,獲得 1 贊
南懷瑾老師:這四種難行之行都真的做到了,就是菩薩再來
真修行,必須於行、住、坐、卧四威儀中處處體會、修證“達摩四行觀”:一、報冤行,二、隨緣行,三、無所求行,四、稱法行。
一、什麼是“報冤行”?
我今天活在這世上,人家罵我、辱我、欺我、怨我,都能冤親平等視之。一切遭遇,無論是父母、兄弟、朋友、仇敵對自己的種種,都能瞭解此乃過去所欠之恩怨,應該還的,所以寒山問拾得:“世人謗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輕我、賤我、惡我、騙我如何處治乎?”拾得答:“只要忍他、讓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、不要理他,再待幾年,你且看他。”
如此作到一切冤親平等,受了大辱都很坦然,也就同於《金剛經》所説的“是人先世罪業,應墮惡道,以今世人輕賤故,先世罪業,即為消滅。”一切都是報冤行,真修行要隨時存念:“我欠這世上的債還沒了,我是來還債的。”一般人能這麼想到、做到嗎?——難!
二、什麼是“隨緣行”呢?
有好的衣服就穿好的,沒有就穿差一點的,甚至一無所有,從垃圾堆裏撿來縫縫補補,也可以穿,一切隨緣。寒山又問拾得:“還有甚訣,可以躲得?”拾得答:“我曾看過彌勒菩薩偈,你且聽我念,偈曰:老拙穿衲襖,淡飯腹中飽。補破好遮寒,萬事隨緣了。有人罵老拙,老拙只説好。有人打老拙,老拙自睡倒。涕唾在面上,隨他自幹了。我也省力氣,他也無煩惱。”
有人罵我,我説:“好!好!我該罵”,有人打我,我就躺下來給你打,免得被你打,還花了那麼大的力氣,你也少煩惱,這多好,這又多難做到,此即隨緣行。
昨天有個出家人問我:“有人邀我到法國閉關好不好?”我説:“真修行,污泥中也可以閉關,我前幾年不就在鬧市中閉了三年關?!”當時我也曾到處找地方,後來有個桃園的同學,要把竹林老家都送給我,我到了那裏,自覺好笑,就回來街上閉關,自己嘲笑自己:“昏了頭!哪裏不是道場,提婆達多不也是以地獄為道場嗎?!”
三、什麼是“無所求行”?
你們在此修行做什麼?想成佛是不是?自性本空,一切都還是還債,前生欠的宿債,所有恩怨、感情都是還債,這個因果錯綜複雜,不過也有蛛絲馬跡可尋。欠多了來生做人父親,白手成家,辛辛苦苦經營賺了些錢,等兒女長大,自己就翹辮子了。你們的父母哪個不欠你們的,十月懷胎,辛勤養育,你卻頭髮一剃,自己去修行,這些債主都來還你的債,如果不好好修行,你又還他們什麼呢?一無報養,來生的債就欠大了,甚至也有來生變頭母豬,生一大堆小豬去還債的啊!
所以,真大徹大悟者,佛也不成,凡夫也不做,大家想象得到嗎?有人問我:“幾時出家?”我説:“我從未入過家。”什麼叫家?一個男的,一個女的,兩個鋪蓋湊在一起,這叫做結婚成家,然後幾年下來生了一堆所謂的“孝子賢孫”,長大了各奔東西。修行要清醒啊!什麼叫家?——沒有家!所以不用出世,也不用入世。真修行人,一切佈施,無所求,不想收回,不成佛亦不做凡夫,就是禪宗所標榜的“無心道人”。所謂:“無佛處莫留戀”——空也不住,“有佛處急走過”——有也不守。要如此反省念頭,一落二邊就錯了。
像你們有時做勞務,搬椅子或掃地、擦窗户什麼的,看看別人好好地在打坐,便想偷懶,別的同學那麼舒服,我又何必這樣的苦幹呢?這就是“抱”怨行,不是“報”怨行,是有所求行,也沒做到隨緣行。大家檢點平常對念頭有如此反省嗎?有此念頭要懺悔、要舍念。
四、什麼是“稱法行”?
起心動念,講話、態度、行為等等,沒有不合佛法的。待人應恭敬、謙虛、慈祥,處處如此而行。但是沒有慈祥,不一定不稱法,怒目金剛也有深妙的道理在。
因此,如何夠得上稱法行?如何才不犯大乘戒?就要靠智慧抉擇應用了,不是光打坐、三際託空就可以成佛,見個空性有什麼用?自性本空,如果八十八結使的業力轉不過來,那是永遠成不了佛的。
修行人一顰一笑都要適當,不該笑時你笑,不該皺眉頭時你皺眉頭,都錯。起心動念都要注意,有些人自以為心如止水,如果忽然驟起波濤,誰也都莫可奈何!別以為心如止水就到了,所謂:“户樞不蠹,流水不腐”,止水不動會發臭的。有人在山頂上住洞閉關,一下山來,受到凡塵外境的誘惑,那在山頂上一味清靜一下就垮了,這些都是修行人的苦境。
所以,菩薩行是一顰一笑都要清清楚楚,念念舍,提得起放得下,若能“懲忿窒欲”慣了,一上座用不着求定即在定中,此乃自性大定,盤不盤腿都無所謂,即是“不是息心除妄想,只緣無事可思量”,“清淨本然,周遍法界”,此即如來大定,知道嗎?
《修行人的本分——達摩四行觀》
-------------
達摩大師以“四行”而概括大小乘佛學經論的要義,所謂“四行”,就是“報冤行、隨緣行、無所求行、稱法行”四行。不但為中國禪宗精義的所在,而且也是隋、唐以後,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化融會為一的精神之所系。可惜後來一般學禪的人,看祖師的語錄、讀禪宗的史書等,只喜歡看公案、參機鋒、轉語,而以為禪宗的宗旨,盡在此矣。殊不知錯認方向,忽略禪宗祖師們真正言行。因此,失卻禪宗的精神,而早已走入禪的魔境,古德們所謂“杜撰禪和,如麻似粟”,的確到處都是。
(一)所謂“報冤行”
這就是説,凡是學佛學禪的人,首先要建立一個確定的人生觀。認為我這一生,來到這個世界,根本就是來償還欠債,報答所有與我有關之人的冤緣的。因為我們赤手空拳、赤條條地來到這個世界上,本來就一無所有。長大成人,吃的穿的,所有的一切,都是眾生、國家、父母、師友們給予的恩惠。我只有負人,別人並無負我之處。因此,要盡我之所有,盡我之所能,貢獻給世界的人們,以報謝他們的恩惠,還清我多生累劫自有生命以來的舊債。甚至不惜犧牲自己而為世為人,濟世利物。大乘佛學所説首重佈施的要點,也即由此而出發。這種精神不但與孔子的“忠恕之道”,以及“躬自厚,而薄責於人”的入世之教互相吻合,而且與老子的“生而不有,為而不恃”的效法天道自然的觀念,以及“以德報怨”的精神完全相同。
達摩大師自到中國以後,被人所嫉,曾經被五次施毒,他既不還報,也無怨言。最後找到了傳人,所願已達,為了滿足妒嫉者仇視的願望,才中毒而終。這便是他以身教示範的宗風。以現代語來講,這是真正的宗教家、哲學家的精神所在。蘇格拉底的從容自飲毒藥;耶酥的被釘上十字架;子路的正其衣冠,引頸就戮;文天祥的從容走上斷頭台等事蹟,也都同此道義而無二致。只是其間的出發點與目的,各有不同。
原始在印度修習小乘佛學有成就的阿羅漢們,到了最後的生死之際,便説:“我生已盡,梵行已立,所作已辦,不受後有。”然後便溘然而逝,從容而終。後來禪宗六祖的弟子永嘉大師在《證道歌》中説:“了即業障本來空,未了先需償宿債。”都是這個宗旨的引申。所以真正的禪宗,並不是只以梅花明月,潔身自好便為究竟。後世學禪的人,只重理悟而不重行持,早已大錯而特錯。因此達摩大師在遺言中,便早已説過:“至吾滅後二百年,衣止不傳,法周沙界。明道者多,行道者少。説理者多,通理者少。”深可慨然!
(二)所謂“隨緣行”
佛學要旨,標出世間一切人、事,都是因緣聚散無常的變化現象。“緣起性空,性空緣起”,此中本來無我、無人,也無一仍不變之物的存在。因此對苦樂、順逆、榮辱等境,皆視為等同如夢如幻的變現,而了無實義可得。後世禪師們所謂的“放下”、“不執著”、“隨緣銷舊業,不必造新殃”,也便由這種要旨的扼要歸納而來。
這些觀念,便是“淡泊明志,寧靜致遠”的更深一層的精義。它與《易經·繫辭傳》所謂:“君子所居而安者,易之序也。所樂而玩者,爻之辭也。”“居易以俟命。”以及老子的“少私寡慾”法天之道,孔子的“飯蔬食,飲水,曲肱而枕之,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,於吾如浮雲”等教誡,完全吻合。由此觀念,而促使佛家許多高僧大德們“入山唯恐不深”,“遁世唯恐不密”。由此觀念,而培植出道、儒兩家許多隱士、神仙、高士和處士們“清風亮節”的高行。但如以“攀緣”為“隨緣”,則離道遠,雖然暫時求靜,又有何益?
(三)所謂“無所求行”
就是大乘佛法心超塵累、離羣出世的精義。凡是人,處世都有所求。有了所求,就有所欲。換言之,有了所欲,必有所求。有求就有得失、榮辱之患;有了得失、榮辱之患,便有佛説“求不得苦”的苦惱悲憂了。所有孔子也説:“吾未見剛者。”或對曰:“申棖。”子曰:“棖也欲,焉得剛。”如果把孔子所指的這個意義,與佛法的精義銜接並立起來,便可得出“有求皆苦,無欲則剛”的結論了。
倘使真正誠心學佛修禪的人,則必有一基本的人生觀,認為盡其所能,都是為了償還宿世的業債,而酬謝現有世間的一切。因此,立身處世在現有的世間,只是隨緣度日以銷舊業,而無其他的所求了。這與老子的“道法自然”,以及“不自伐,故有功。不自矜,故長。夫唯不爭,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”乃至孔子所謂“富而可求也,雖執鞭之士,吾亦為之。如不可求,從吾所好。”都是本着同一精神,而從不同的立場説法。但是後世學禪的人,卻以有所得的交易之心,要求無相、無為而無所得的道果,如此恰恰背道而馳,於是適得其反的效果,當然就難以避免了。
(四)所謂“稱法行”
這是歸納性的包括大小乘佛法全部行止的要義。主要的精神,在於瞭解人空、法空之理,而得大智慧解脱道果以後,仍須以利世濟物為行為的準則。始終建立在大乘佛法以佈施為先的基礎之上,並非專門注重在“楖慄橫擔不見人,直入千峯萬峯去”,而認為它就是禪宗的正行。
以上所説的,這是達摩禪的“正行”,也便是真正學佛、學禪的“正行”。無論中唐以後的南北二宗是如何的異同,但可以肯定地説一句:凡不合於達摩大師初傳禪宗的“四行”者,統為誤謬,那是毫無疑義的。如果確能依此而修心行,則大小乘佛學所説的戒、定、慧學,統在其中矣。
《禪話》